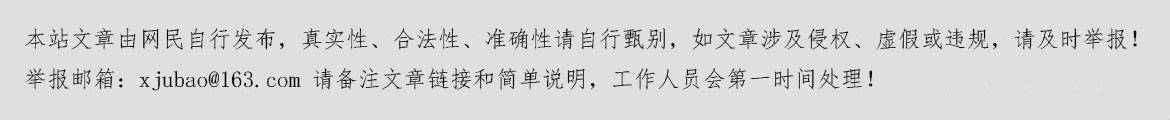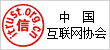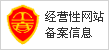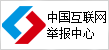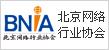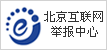“音乐灵魂”黄家驹:他的落寞比你想象中还要无奈
2021-11-25 12:34:15
1991年,Beyond乐队彻底大红,成为第一支在香港红磡开演唱会的乐队。也是在那一年,家驹说出了那句经典名言:“香港只有娱乐,没有乐坛。”
随后,Beyond远赴日本,去追寻那心中的音乐殿堂,“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……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”。
那时的家驹没有想到,此行成为了他人生的最后旅程。正如后来那首经典的《海阔天空》所述:“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。”
而《海阔天空》,也成了他的绝唱。
1993年6月24日,日本时间凌晨一点,黄家驹参加富士电视台一档游戏节目的录制,跌落舞台,头部着地。昏迷数日后,6月30日离世。
记者会上,家驹的弟弟黄家强抱头痛哭,直言宁可意外发生在自己身上。
家驹去世之后,罗大佑用同样的格式作出评断:“香港没有真正的音乐人,除了黄家驹。”
黄家驹,一个把音乐视为生命的人,为什么如此决绝地离开香港远赴日本,却走进了自己最为厌恶的娱乐节目中,最终又陨落于此。
黄家强回忆起其兄当年话语:“乐队必须要把音乐的水平放低一点,做得更简单,吸引到普通歌迷后,才能有更多资本去做自己喜欢的音乐。”
一些理想主义者认为这是黄家驹的妥协,但在黄家强眼里,这种妥协,其实是另一种坚持:“不是妥协,是适应。”
只是这种坚持的代价,未免太残酷了些。
黄家驹曾有过这样的感慨:“我觉得每一样东西都是发自内心,要感动别人一定要先感动自己,我是音乐人,我会尊重音乐。如果没有音乐,我会死,我真的会死,不可能没有。”
“我整天觉得自己背着吉他就好像背着一把宝剑。”
他的“宝剑”是在17岁那年很偶然地获得的。
那一年,邻居搬家丢弃了一把破吉他,被黄家驹从垃圾堆中捡了回来。清理干净后,家驹把它送给喜欢弹吉他的好友。
对方很是感动,然后拒绝了他的好意,因为吉他实在太破了。
无奈之下,黄家驹自己留下了这把“宝剑”。无心之举,开启了华语乐坛的一个神话。
舍不得丢掉破吉他的黄家驹,开始在家里自己弹奏练习。渐渐地,他喜欢上了这种感觉。
自觉有成的黄家驹加入了一只地下乐队,却被主吉他手狠狠地羞辱:你弹得奇差无比。
正值青春期的黄家驹深受刺激,那时的他叛逆而执着,至此开启了疯魔般的练习模式。
开始的时候,木吉他的弹奏并不算太吵,家人也就听之任之。但黄家驹并不满足于此。在他存钱买了一把二手电吉他后,家里开始充斥着震耳欲聋的噪音。
在家人的强烈谴责之下,他默默地买了耳机,每天戴着耳机静静地坐在凳子上,一弹就是几个小时。
在黄家驹吉他水平突飞猛进的同时,Beyond乐队的其他伙伴,也在赶来的路上。
黄家驹最早认识的是吉他手邓炜谦,这是一位对Beyond乐队取名有着决定性影响的早期成员。
邓炜谦比黄家驹大三岁,当时在音乐上也懂得比较多,他启发了黄家驹从传统摇滚到前卫艺术摇滚的认知。
另一边,在通利琴行老板的介绍下,家驹认识了叶世荣,一位同样深受国外摇滚影响的架子鼓手,俩人一见如故。
再后来,黄家驹的另一位好友李荣潮也加入进来。四人形成组合,李荣潮弹贝斯,叶世荣打鼓,邓炜谦是主音吉他,家驹担任主唱兼节奏吉他手。
1983年,当黄家驹无意中看到香港《吉他杂志》举办第一届“山叶吉他大赛”的宣传海报时,他有种预感,自己一直在等待的机会要来了。
临时起意的黄家驹和叶世荣决定参加大赛,但那时乐队组合连个名字都没有。
当时的音乐主流还是以Rock&Roll为主,邓炜谦想做一支“BeyondRock&Roll”的乐队,就是摇滚以外的一个音乐范畴。
于是,一个影响了无数年轻人和吉他爱好者的名字诞生了:Beyond!
当时的参赛乐队大都以翻唱为主,坐在台下听众甚至可以听完披头士的一整张专辑。
在这里,Beyond展现出他们独树一帜的风格——坚持原创。
第一届山叶吉他大赛过后,人们记住了一首极具冲击力的歌曲《大厦》,还有夺冠之夜的那首纯音乐——《脑部侵袭》。
Beyond如愿夺得了冠军。
著名乐评人冯礼慈在《一队新乐队启航了——Beyond》一文中写道:
“这两年的大赛中,总有几队乐队由年纪轻轻的小伙子组成,而且玩得头头是道,令人相信,香港乐坛正踏向有希望的道路。”
但那时谁也没有想到,通往希望的道路是如此的坎坷。也正是有着如此的坎坷,Beyond的音乐才华才得以彻底释放,乃至升华,经久不衰。
不管从什么时候来看Beyond,他们都是香港最特殊的存在。他们的歌曲追求原创,内容致力于人文关怀和家国情怀。
Beyond像是独具风格的音乐魔法师,他们将音乐当成一种媒介,将自己的感悟封印其中。
当第一个音符响起时,人们的脑海便会自然映射到这种感悟,那些与之相关的记忆画面,便会一一浮现。
从描述母爱的《真的爱你》,到讽刺社会的《俾面派对》,再到纪念曼德拉的《光辉岁月》,到励志歌曲的《不再犹豫》,到呼唤和平的《Amani》,再到《农民》……
Beyond在保证歌曲琅琅上口的同时,又兼具一定的深度。
而他们最出色的地方在于,在保证了歌曲深度以及传唱度的同时,又尽力拓展了歌曲的广度,这在财富和荣誉唾手可得的娱乐圈尤为可贵。
自出道开始,Beyond就有着自己的坚持,尽管风格一直在变,成员也一直在变,但是初心从未变过。
夺冠半年后,邓炜谦和李荣潮因为家庭和工作原因,相继离开了乐队。幸好,黄家驹的弟弟黄家强及时加入。
“如果不是因为家驹,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玩音乐。”黄家强曾多次这样说。而最初令他反感的,也正是黄家驹所玩的音乐。
在黄家强的记忆里,自从哥哥捡到了那把破“宝剑”后,外出和朋友聚会的时间少了,更多的是留在房间里练习吉他。
黄家强觉得吵,赌气把电视机的声音开大,黄家驹就会弹得更大声。兄弟俩一声不吭,都是默默地用手指较劲。
终于有一天,黄家强被摇滚乐的“好玩”吸引了。开始的时候,他在哥哥的推荐下学习键盘,后来改学贝斯,从此“入坑”。
而邀请家强加入乐队的,却不是哥哥黄家驹,而是叶世荣。
20世纪80年代初是摇滚乐的黄金年代,许多伟大的乐队和音乐人不断涌现。香港也迎来了高速发展期,许多大牌艺人都把香港看作全球巡演不可或缺的一站。
但刚刚拿了冠军、出了合集的Beyond,依然默默无闻。
那时的乐队要想提升知名度,只有两个方式:尽情表演,疯狂参赛。
1984年,黄家驹拉着叶世荣和黄家强四处奔走,哪里有演出,哪里有比赛,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。从澳门到深圳蛇口,再到香港。
在到处演出和参赛的过程中,黄家驹一边观察,一边思考。他发现一个现象,很多乐队都没有键盘手。
键盘手在乐队中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,在演出中负责提供除吉他、贝斯、鼓以外的所有声音。他的弹性很大,你可以要,也可以不要。
然而,键盘手通常是乐队中乐理水平最高的那位,扒谱,编曲这类幕后苦差大多是由他包办。甚至整个乐队,也可以让键盘手包办一切。
黄家驹觉得,一支乐队要想创作出层次丰富的作品,必须要有一个好的键盘手,为此他特意在报纸上刊登了招募键盘手的信息。
不久,陈时安加入乐队,成为主音吉他手。
这也是一位很特殊的存在,他的创作才华与黄家驹几乎不相上下,《myth》和《永远等待》这两首歌就是陈时安参与创作的作品,收录在《再见理想》中。
不过,陈时安时期的Beyond演出并不频繁,留下的现场照片极为少见,很多乐迷对他都没什么印象。家驹为了怀恋这位好友,在《永远等待》这张唱片的歌词内页用了三张他的远景照片。
陈时安在Beyond呆了不到一年便离开了,他要出国深造。
陈时安告别之际,Beyond正在准备他们的首场独立演唱会。这让黄家驹很苦恼,短时间内哪能找到替代陈时安的吉他手呢?
帮忙设计海报的黄贯中进入了大家的视野,他的吉他技术很不错。这样,经过几番波折之后,乐队的成员总算固定了下来——黄家驹、叶世荣、黄家强、黄贯中。(后期还有一位吉他手兼键盘手刘志远曾短暂加入)
起初,为了谋生,Beyond四人并没有全职作音乐。黄家驹做过办公室助理、纺织厂采购,最后在叶世荣的介绍下,来到保险公司做销售员。
在黄家强的印象中,家驹的业绩并不好。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完成公司规定的保险单数,不够的时候,他就去拼命地找客人,找够了就回去接着练吉他。
不过,这段经历对黄家驹的帮助一点也不小,本就无比执着的他,借助销售员的经历,练就了无比坚定的口才。
在Beyond乐队里,黄家驹是灵魂人物,其他三人则是黄家驹坚定的支持者。因为就算反对也无效,他们吵不过销售员出身的黄家驹。于是,他们跟着一起执着。
他们平常练习的地方,在深水埗洗衣街215号二楼,这个被称为“二楼后座”的地方,其实是叶世荣家的房子。
当时为了能有一个大本营,叶世荣谎称要结婚,把房子从父母手中骗了过来。
Beyond每天的练习惹得邻居们不胜其扰,从指责、谩骂到报警、搬家。最后,Beyond熬走了这栋楼的大部分邻居。
首场演唱会,Beyond并不顺利。演唱会在港岛明爱中心举行,从租音响到画海报再到卖门票,所有台前幕后工作都是乐队成员自己完成的。
表演还没结束,观众就走了一大半,最终以亏损几千块钱而告终。
不过,祸兮福所倚,福兮祸所伏。那场演唱会引发了另一位重要人物和Beyond的交集。
这个重要的人物就是资深音乐发烧友和著名经纪人陈健添,他当时是浮世绘和小岛乐队的经纪人,也是后来王菲星路上最大的伯乐。
陈健添那时并不欣赏Beyond,因为那时他们的风格偏重型音乐,不注重旋律,皮衣长发的打扮也让人感觉痞痞的。
但是很奇怪,脑海中有个声音告诉陈健添,这四个人以后一定会火。他鬼使神差地找到Beyond,签下了他们。
后面,总是赔钱的Beyond迎来了意外之喜。
他们和小岛乐队一起,受邀到台湾参加“亚太流行音乐节”。在那里,他们受到了乐迷们的热烈追捧。
按照原定安排,Beyond和小岛在7月23、24日演出两天,但由于Beyond的表演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反响,主办方安排他们25日加演一场。
欣喜之下的黄家驹继续发扬他的风格,又做出了一个执着的决定——自费出唱片。
又是一段贴海报、发传单、谈售卖、送货上门的日子,Beyond的第一张专辑诞生了——《再见理想》。
有人说,《再见理想》是最能体现Beyond才华的专辑,囊括了英语、粤语、纯音乐,贡献了《再见理想》、《旧日的足迹》这样经典的歌曲。
再见了理想还得回归现实,大家一算账,每人赚了240块。虽然赚得很少,但这是一个标志,他们赚钱了,有了源源不断坚持下去的动力了。
在那之后的Beyond终于签约了唱片公司,制作了第二张专辑《亚拉伯跳舞女郎》。这张充满中东风情的粤语专辑,对当时的乐坛而言是个大胆的尝试。
但一身雷人的装扮加上异域风情的曲风,对于听惯了芭乐情歌的港人来说,接受程度可想而知。
第三张专辑《现代舞台》同样销量不佳,公司坐不住了,对他们发话:“再出一张还不行,就再也没有机会。”而他们那时也窘迫到换琴弦的钱都没有。
Beyond开始逐渐向市场靠拢,剪去了长发,调整了创作方向。正如黄家驹所说:
“乐队必须要把音乐的水平放低一点,做得更简单,吸引到普通歌迷后,才能有更多资本去做自己喜欢的音乐。”
1988年,第四张专辑《秘密警察》问世,其中的《大地》获得香港无线电视台“十大劲歌金曲”大奖。
《大地》这首歌的初始版本叫《黄河》,就在前一年,黄家驹曾想把它放进《永远等待》这张唱片中。
不过,家驹的想法被陈健添拦住了,他说现在推出这样的歌还不是时候。事实证明,陈健添的眼光确实很独到,他知道在什么时期推出一首好歌,能让它价值最大化。
这张专辑中还有另一首很有故事的歌——《喜欢你》。歌曲的女主角是家驹的女友,他们在相恋时早已谱好了曲子。
但随着Beyond的音乐事业逐渐有了起色,家驹变得越来越忙,忽略了女友的感受,两人最终分手了。
据说当时女友向黄家驹提出要求:只要他能放弃音乐,自己便跟他走。家驹十分为难,为了挚爱的音乐,他选择放弃爱情。
心怀愧疚的家驹有感而发,为《喜欢你》填上了伤感的歌词,表达因为忽视而失去爱情的痛苦与自责:
“喜欢你/那双眼动人/笑声更迷人……满带理想的我曾经多冲动/屡怨与她相爱难有自由……”
这首歌也在当年登上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榜,成为了乐队的代表作之一。
Beyond也在这一年真正为香港人所广泛认知。从出道到被熟知,Beyond用了整整五年。
而严格意义上讲,这一年才是黄家驹真正“出道”的年份。如此算来,他在公众认知下存在的时间,一共只有5年。
这5年里,《真的爱你》、《午夜怨曲》、《灰色轨迹》、《光辉岁月》、《AMANI》、《不再犹豫》、《长城》、《农民》、《遥望》、《海阔天空》等经典作品先后问世。
其中最为卓越的作品《海阔天空》、《光辉岁月》,词曲都是黄家驹亲自操刀。和他的作曲成就形成张力的,是他不懂乐谱(指的是五线谱,并非不懂乐理);而和他的歌唱水准两相对比的,是他从未接受过专业教育。
他的“御用词人”刘卓辉感慨:“去了趟非洲回来就能写出《光辉岁月》和《AMANI》这么好的歌曲,除了天才,还能说什么。”
1991年,Beyond已经凭借《大地》、《真的爱你》、《光辉岁月》连续拿下了第6、7、8届十大劲歌金曲奖,成为乐坛巨星。但是他们发现,成名之后更加迷茫。
90年代的香港,电视综艺节目几乎如出一辙地遵循这样的套路:找几个娱乐圈的红人,玩一些非常低智能的游戏。比如知识问答、光着脚踩在布满坚硬的凸起的地而上看谁坚持得久等,输了的被疾风吹面,或者冷水淋头。
这种毫无营养的节目,却是一种“三赢”的工具:电视台提高收视率、明星增加曝光率、观众看到了明星。
已成为香港超一流的乐团的Beyond也不能免俗,他们同时跨足影视和音乐,行程非常忙碌。
而在黄家驹看来,这些无聊游戏过多地占据了他们的创作时间,一个音乐人在舞台上扮演小丑博人一笑,也有损尊严。“虽然红了,但不开心,要做很多无聊的事情。”
为此,黄家驹还专门写下了既严肃又诙谐的《俾而派对》(意为“赏脸聚会”),讽刺那些热衷于宣传游戏的艺人:“不管相识不相识,尽管多些Sayhello,不需诸多的挑剔,无谓太过有性格,派对你不缺席。”
他说:“好奇怪,有些艺人能够装出笑脸,明明彼此不是很熟,见而时却互相拥抱假扮亲热,为什么?我就不愿意做木偶,对人强颜欢笑,音乐人只需要做好音乐。”
而《俾面派对》这首用来讽刺演艺圈光怪陆离现象的歌,却被各大电台DJ推崇,高居当年流行榜榜首。
也许,高雅和鄙俗,本就是共生的。
执拗至死并不值得骄傲,知道前路艰难险阻,能够抛开成见奋勇前行,才是真的勇士。
在红磡的演唱会上,与表演同样精彩的,还有家驹演唱前说的那些感人的话:
“大家都觉得很奇怪,通常演唱会都有一些特别嘉宾坐阵,我们Beyond没这么大的面子请到特别嘉宾。
但是我们很开心很开心,找来一大班很特别很特别的嘉宾,我们今晚的特别嘉宾就是红磡体育馆里边全场的观众!”
演唱会后,在Beyond在香港最炙手可热的年份,他们选择了出走日本。
黄家驹憧憬的是,成熟的日本市场,应当是属于音乐人的一片应许之地,去日本发展,就可以逃开这一切令人痛恨的枷锁。
不过,日本的生活和Beyond想象的并不一样。
由于语言不通、文化迥异,他们集体陷入了苦恼、萎靡。叶世荣学会了抽烟,黄家强靠打电动游戏过日子,滴洒不沾的黄贯中爱上了饮酒。
内心最为强大的黄家驹,也遇到了瓶颈。他坚持创作,却产出寥寥,对弹琴也减少了兴致:“吉他放在那里就不想碰,整个人情绪有一点低落,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。”
时代的枷锁,紧紧地扣在Beyond每个人脖子上。
他们努力反抗而不得解放,但他们一直在歌曲里关注一种“冲开一切”的澎湃力量。
在这种压抑的张力下,Beyond推出了两张专辑:《继续革命》和《乐与怒》。
《继续革命》中的两首歌曲:《长城》和《农民》传唱一时。
《乐与怒》中有一首歌叫《遥远的梦》,让Beyond在日本彻底打响,它还有个中文版,叫《海阔天空》。
这首歌写尽了Beyond十年的心路历程,但谁能想到,这首歌竟成了黄家驹的绝唱。
其中的一句歌词“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”,就像是一个魔咒,预示了他将来的命运。
眼看Beyond在日本声名乍起,公司趁热打铁,要增加他们的曝光率和知名度,办法和香港是何其地相似:参加各种电视游戏。
正是这一切,让他们所追逐的自由之梦,彻底变成“遥远的梦”。
Beyond起初以为日本比香港有更大的自由度去做音乐,结果发现,日本就是一个变大了几十倍的香港。
他们依然要参加不喜欢的游戏节目,要装“邻家的小男孩”去得到日本乐迷认同。
黄贯中曾愤怒地说:“来日本不就是为了大一点的天空吗?大一点的天空不就是意味着不用玩游戏吗?结果来了还是玩游戏。日本这个市场,摇滚是一个假象,比香港那个更烂。”
黄家驹也十分后悔。美国诗人埃德娜·米莱的一句话最适合形容此时的黄家驹的心情:“生活不是一桩接一桩该死的事情,而是同样该死的事情的不断重复。”
对自由的追寻,结果只是让他进一步意识到自由的重要。
1993年6月23日晚,乐队的共同好友刘宏博正在Beyond香港的排练室“二楼后座”里弹吉它,接到家驹从日本打来的电话。
家驹在电话里说着说着就有点想哭,身上有一种“无休止的压力”。在香港,累的时候身边有朋友,有熟悉的环境让他可以松弛下来,在日本什么都没有。
他觉得这一年多受到的限制太多,很怕如此做下去,会违背做音乐的初衷,他宁愿选择回到香港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音乐,哪怕是纯音乐也好。
那天晚上他们在电话里谈了四五个小时,临近通话结束,刘宏博问家驹一会儿干什么去,家驹说准备去上一个节目。
6月24日凌晨1时(香港时间半夜12时)。
Beyond在东京富士电视台拍摄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游戏节目“Ucchan-nanchannoyarunarayaraneba”(想做什么就做什么)。
在“对决Corner”的游戏环节中,当天12名嘉宾分成两组,在一个舞台上进行比赛。舞台高约3米,台中央有一个水槽,上空悬缀“宝物”,由两组人争夺。
比赛进行了15分钟,两队人集中到台的一方,由于台上湿滑,有些人滑倒并撞向台后的背景板,过大的冲力导致背景板后的支架脱落,节目主持人和家驹分别坠落地上。
主持人仅受轻伤,并无大碍;家驹不幸头部先坠地,陷入了昏迷。
6月30日,东京的天空下着小雨。
上午,日本媒体还在风传“黄家驹的情况稳定”,“我们也无能为力,只有为他祈祷”。
当天傍晚,富士电视台宣布了噩耗:
“黄家驹先生,香港摇滚乐队Beyond成员之一,不幸在游戏节目中由台上跌下,其后被送到东京女子医院救治,但由于头部受到重伤,于6月30日下午4时15分与世长辞,他的家人和Beyond的其他成员都在医院陪伴他到最后一刻。”
一代香港乐坛天才,就此陨落。
为了获得自由,黄家驹逃离被誉为亚洲最自由之地的香港,前往异国他乡,最终却陨落在他想要挣脱的枷锁中,这是命运所开的玩笑。
“仍然自由自我,永远高唱我歌。”
曾经有一种声音说,黄家驹歌声的经久不绝,得益于死亡的助力。这没有什么值得反驳的,因为这种逻辑,黄家驹早已说得明白:人们眼里只有娱乐没有音乐。
人们大都会有个善良的习惯,把一些已经退出生活的东西视为经典。在各种纪念日中,那些看过的电影、听过的歌,被以经典的名义一一怀旧,尽管它们已与当下的生活无关。
躺在过去的只是资料,能够触动心灵的,可以称之为回忆。
而从过去一路走来,至今依旧生机蓬勃,能够和沿途的人们进行持续心灵对话的,才是经典。
在香港,至少有一个人符合这一条件,他叫黄家驹!
谨以此怀念我们心中不曾失去的梦!